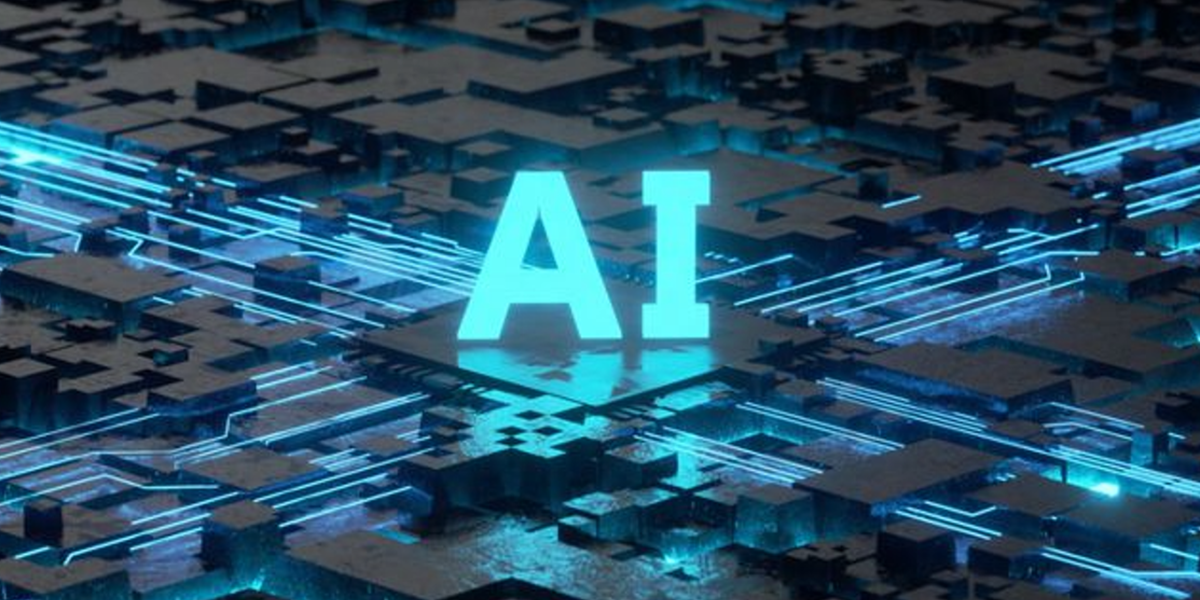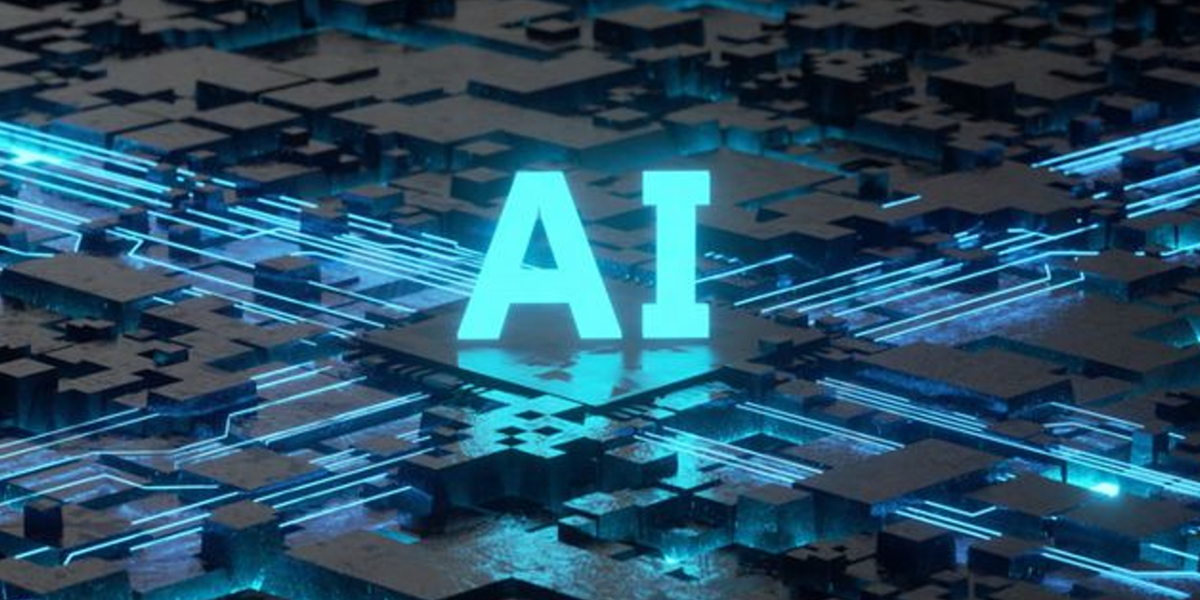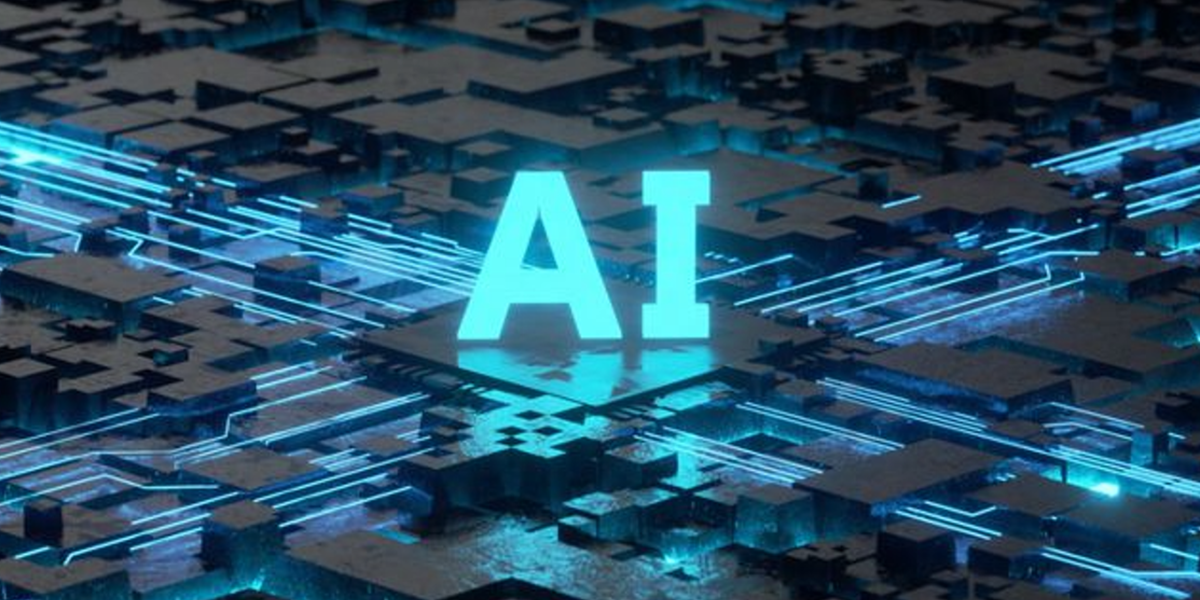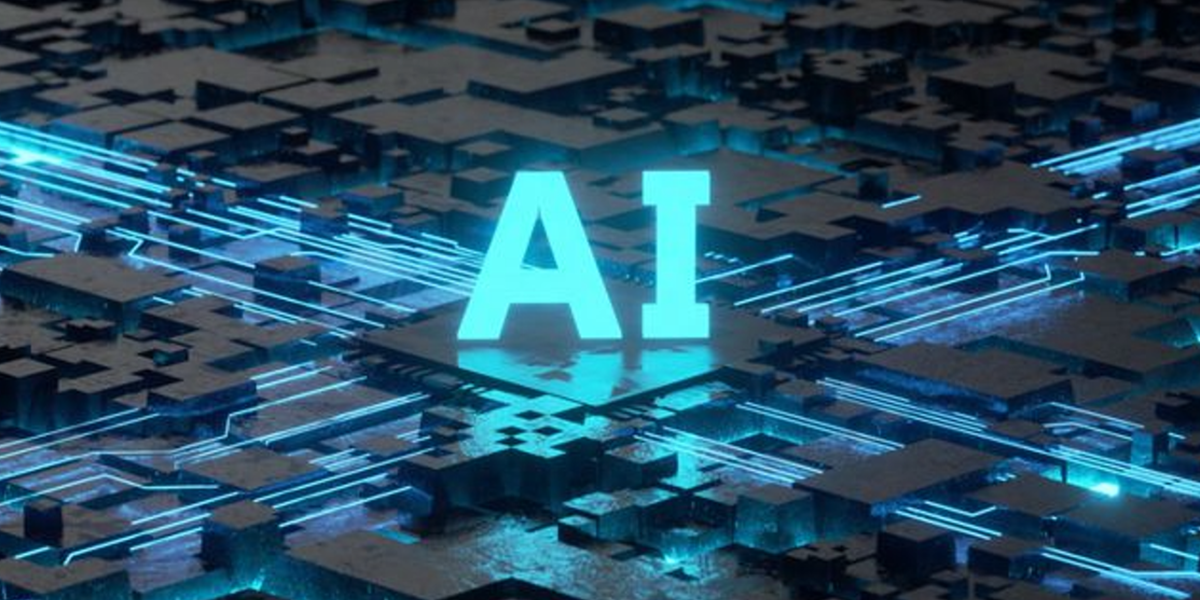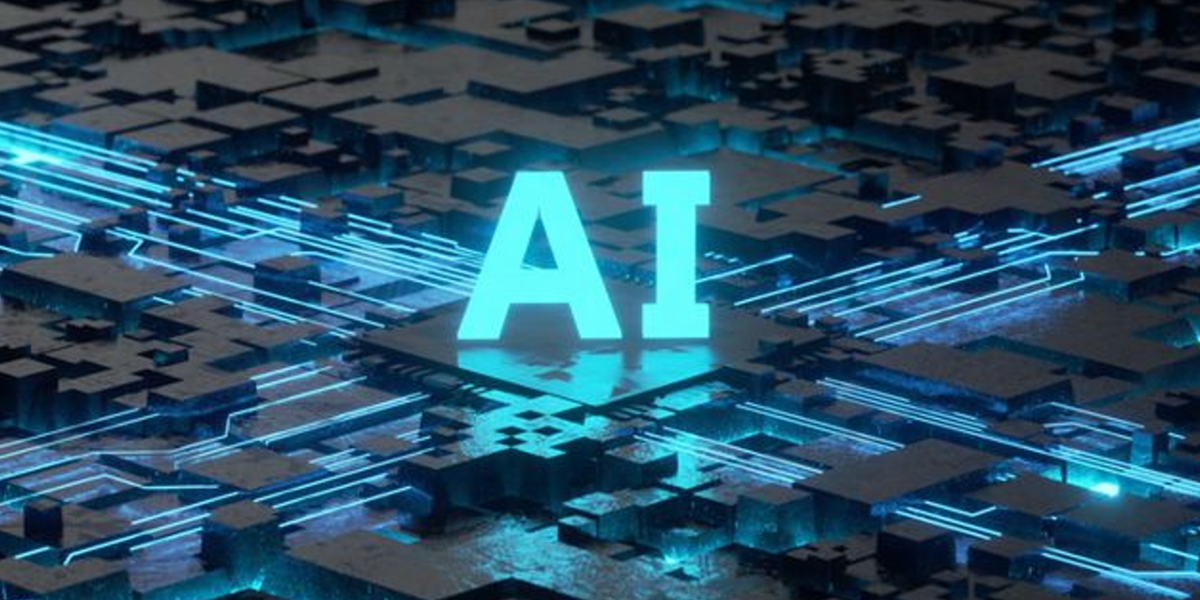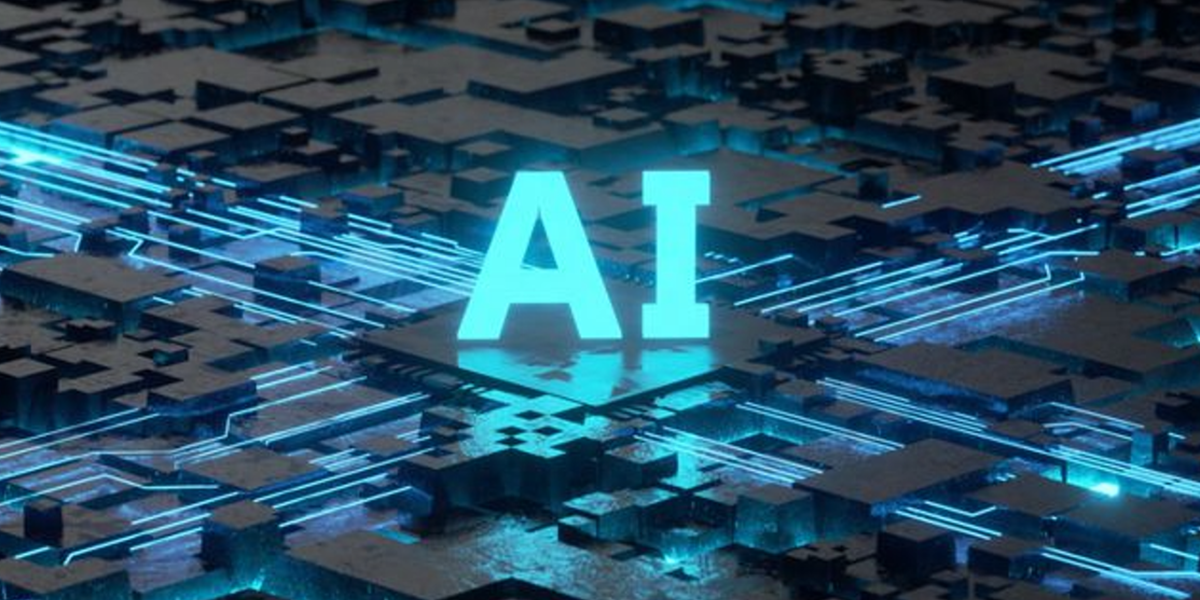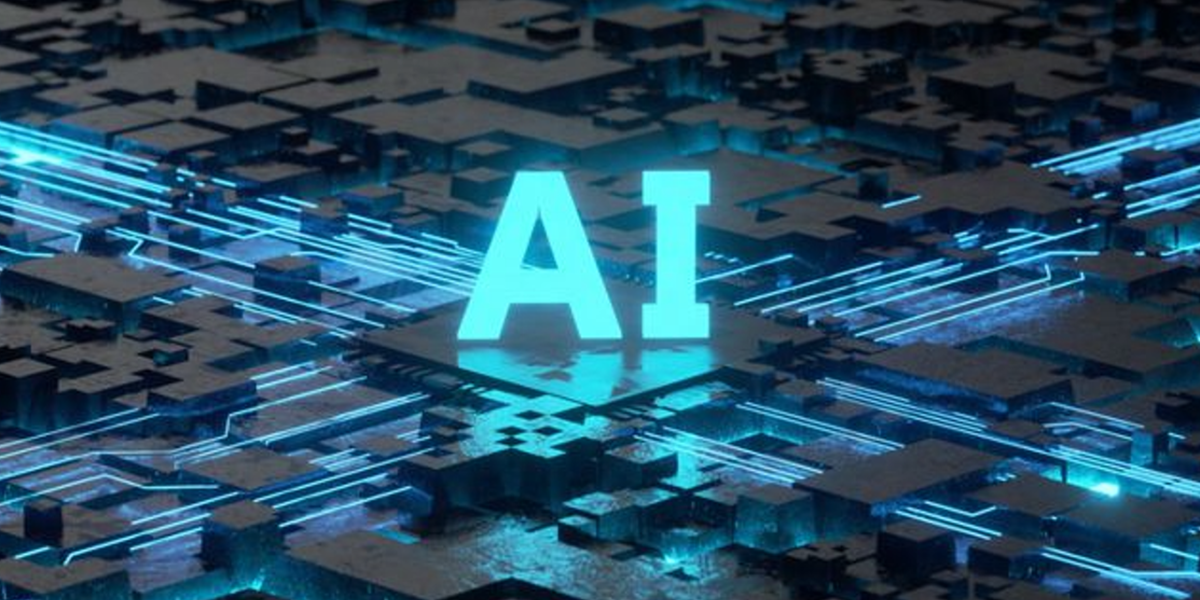新圈地运动与智能产业的未来战略
德国传播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曾将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因为这些二十世纪初期的技术物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人类的感觉器官,打字机介入了人类的触觉,电影介入了人类的视觉,而留声机介入了人类的听觉。在其看来,现代性就是不断用新的技术物来代替人类有限的身体能力,去触碰更广阔的社会。或者可以将基特勒的隐喻延伸到今天的DeepSeek。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我们的思维,并协助我们进行思考,这并不代表着人类丧失了自己的本质,相反通过DeepSeek的介入,人类认知与创造的疆界得到拓展,这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也是一种新质创造力,而这个新质创造力的基础,就是DeepSeek广泛建立的普遍的人与物、物与物关系的物体间性的认识论基础。DeepSeek犹如数字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了赫淮斯托斯的薪火。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认识到,通过DeepSeek等大模型缔造的广域物联网和人与物交互关系所形成的云端王国,并不是一个充满浪漫化色彩的理想王国。互联网世界未能像托夫勒和尼葛洛庞帝[10]在二十世纪末期所预想的那样,为人类带来解放,使其彻底摆脱沉重劳役的枷锁,从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土地一样,云中的土地也不是平整的,它有岛屿、有山丘、有海洋、也有大陆与大陆之间联系的桥梁,这意味着云端的世界也是一个地形学的世界,与现实中的地形学无异。此外,云端的地形学不仅与现实世界中的大地在地形上相似,其或许也可以被私人或国家权力所占有,成为政治统治和资本榨取的资源。正如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到的:“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11]在卢梭看来,在古代社会原始的公地(ager publicus)被某些人圈占,成为了私有土地或私有财产,这不仅意味着私有制的诞生,也为古代以降的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在今天,我们或许将卢梭的名言略改一下,就可以适用于当今云端王国和互联网世界的状况:“谁第一个圈出一块云端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数字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这意味着,互联网的云端世界,正在重复着人类古老文明的起源,即通过圈地运动,重新分配云端世界的地盘,重新按照所占有的土地的大小,确立在云端世界的格局。
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借用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的陆地国家向海洋国家过渡的历史,说明了之前的帝国都是领土国,只是将陆地上的土地视为领土,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海洋主权的新范畴。所有参与大航海的国家,都深切感受到海洋同样是主权可及的领域,主权国家对海洋的管辖实践与权力,直接推动了国际法中领海概念的诞生。在解释了近代国家从领土到领海再到领空的演变历程后,布拉顿敏锐地指出,今天出现了一块新的“领土”,这就是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络发展起来的新领域,即云端的王国,其同样可以被圈地,“今天,行星尺度计算的持续出现(如果仍处于萌芽阶段)可能代表着一种类似的突破和对政治地理秩序的类似挑战。它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云空间是一块有待殖民的新大陆,还因为作为一种空间,它突破了施米特形而上学对地缘政治空间和理论的基本分野——领土和领海区分”。[12]这揭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新圈地运动”(New Enclosure)现象,云空间如同现实土地一般被大公司、大平台、互联网企业竞相圈定,它们将这些地盘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并向使用者不断征收租金,而这成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诱因。
技术封建主义由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学者在2020年提出,深刻揭示了数字云空间中的新圈地运动。正如瓦鲁法基斯所指出:“在‘新圈地运动’的世界里,你经常被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交给数字领域中被围起来的一部分,比如Uber、Lyft或其他一些私人公司。当你要求搭车去机场时,他们的算法会派出自己选择的司机,以期最大化拥有算法的公司从你和司机身上获取的交换价值。这些‘新圈地运动’实现了对数字公域的掠夺,推动了云资本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13]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论价值,并不在于其借用“封建主义”这一历史概念来描绘当下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数字阶段和智能阶段时形成的历史倒退,而在于揭示在云端王国空间中对关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瓜分。总体来说,技术封建主义看到的数字平台、大互联网公司,甚至整个主权国家,可以在如下范围内圈地。
对技术和专利的圈地。技术和专利的垄断现象并非数字时代的特有,早在产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就已显现,知识产权体系曾助长了专利圈地,使某些科技公司在垄断某些核心专利后,不用继续开发新的技术,就可以在现有专利垄断基础上不断收取专利费(也是一种专利租金)。在数字和智能时代,技术专利的壁垒仍然存在,并远远超越了之前的时代,但技术专利的垄断并不能完全隔断技术和产业。对于科技产业而言,科技封锁和专利垄断的确会带来一些发展上的迟滞和伤害,但科技发展是多路径和多目的的,这些垄断的专利或许不能短期内被超越,但可能在未来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将原有的专利垄断和圈地“废黜”。
对用户的圈地。这是瓦鲁法基斯等学者关心新圈地运动的主要场域。与技术专利不同,全世界的用户总量存在天然上限,对用户的圈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产业竞争形成降维打击。也就是说,即便一个公司开发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没有大量用户进驻,也难以形成市场影响力。任何需要面对用户的商品,都必须依赖圈定了大量用户的平台才有可能获得市场机会。这一规律对于智能大模型产业也是适用的。大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实验室产品,更在于是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用户的圈定。当DeepSeek得到世界公认时,其价值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与OpenAI层面的用户竞争,而是应广泛介入更多的工业产品,如无人机、智能驾驶、智能机器人,以便形成更广大的实用场景,圈定更大规模的用户群。
对数据的圈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要素,也是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对人工智能发展而言,尤其对于其深度学习和智能训练,数据库和语料库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无论是DeepSeek还是ChatGPT的成功,都建立在占有更为优质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的基础上。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OpenAI已经通过广泛算力取代海量数据优势的情况下,DeepSeek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实现了对数据资源的优化,经过专业筛选的数据库可以更精准、更灵活地处理人类与智能体的交往关系。
对门户的圈地。尽管很多技术封建主义已关注对专利、数据和用户的圈地,但对门户(portal)的圈地,一直相对而言被忽视。从地形学角度来看,重要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联结,往往需要通过相对狭小且十分重要的关隘来实现,如战国时期函谷关和潼关是联结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地,掌握这两处关隘,便可以控制不同地域间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同样,在今天的云空间中,人类并不是直接以语言的方式进入到云空间中,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模型和算法,参与到一种交换的界面,这些在不同界面负责转译的工具和大模型,便成为了门户。正如澳大利亚思想家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所强调:“这些门户似乎管理着可能的事物与声称指挥它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4]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门户已经被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平台所攫取,任何试图通过这个门户进入互联网世界和物联网世界的公司、个体、乃至国家都必须向他们缴纳通过门户的费用,这就是西方大型互联网公司不断获得利润的来源,他们的利润并不来自于生产或科技研发,而是来自于对门户的垄断。DeepSeek的战略价值,正在于其作为核心门户的枢纽地位。
从“新圈地运动”特别是门户圈地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未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价值。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科技产业的发展权,但在互联网的云空间中,无论是以Windows系统连接起来的电脑互联网,还是苹果手机和电脑代表的iOS操作系统,以及隶属于谷歌公司的Android系统,都代表着对门户与数据的垄断和圈地,其他国家如果需要开发自己的产业,就必须不断向这些系统缴纳费用。当然,中国也自主开发出了鸿蒙系统,但鸿蒙系统仍然与Windows、iOS和Android等系统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竞争。未来的智能产业,如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智能驾驶产业,将会产生一个全新的赛道,也会形成新的门户,即链接人类身体与智能物之间的大模型,会成为物联网,或是万物智联的门户,成为将人类与智能体关联起来的门户。通过发展通用大模型,形成中国自主的人类与智能物的链接门户和接口,才能将整个智能产业的发展机遇和趋势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受某些国家和公司技术“卡脖子”的威胁。这既是面对智能产业发展的立场,也是面向未来的智能产业的战略需要。也只有在自主掌控的技术门户、技术生态、技术数据库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23BSK01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2]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3]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5]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90页。
[6]赵汀阳:《替人工智能着想》,《哲学动态》,2023年第7期。
[7]夏马尤:《反思无人机》,焦静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41页。
[8]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9]A. R. Galloway,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31.
[10]参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
[1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12]B.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6, p. 26.
[13]Y.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4, p. 75.
[14]A. R. Galloway, E. Thacker, M. Wark,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60.